

对于准备考研的人来说,一进入12月,意味着迈入了最后的倒计时。“考研对许多人来说,预示着可以得到一个更高的学历,还意味着可以调换到一个更好的学校。”然而,对于下文作者陈志远来说,考研作为一种选择,只是为了“赎身”,从理科生做回文科生。
在1998修订本《新华字典》第673页,有这样一个例句:“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;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;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: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。”这也可以看作人生百态、千万条路,而“只要人生不是数字的比较,不就都有奔头的么?”
《考研日忆往》
陈志远
冬至日,正赶上考研第一天,也是公共课的考试结束。夜幕初降路过北科大西校门,听考生们走在路上对数学题的答案。那景象有点壮观。今年还有位本科同学在我的《续高僧传》读书会上,考研前一周还来跟我们读这,我很感激。问他战果如何?小林回问了一句,老师当年是保送的吧?我突然觉得有好多好多故事想讲。
考研对许多人来说,预示着可以得到一个更高的学历,还意味着可以调换到一个更好的学校。对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,重要的只有一件事,从理科生做回文科生。
考研以后我落下一个心病。直到博士期间还在做这样的梦,梦见我读的这些学位都清零了,又回到高三毕业班,又要考数学、物理了。我原本是以理科参加高考的,并不惧怕这些,考研的科目也没有这些,只是考研把一个闲散的大学生拉回高三的节奏,那种感觉太累心了。

一
我怎么成了理科生呢?这事说起话长,简单地说,我喜欢和聪明人在一起。我高中那个理科班,在文艺方面也比文科班强。可是到了北大,却觉得特别压抑。我的专业是环境科学。这是个新兴的交叉学科,也就是围绕现实的需求,什么都学点,什么都别深究。我们的课程里有水化学、大气物理、分子生物学、生态学、毒理学、环境经济、环境评价,都是浅尝辄止。我是那种学物理恨不得看看亚里士多德和牛顿的人。
大一上半过完,我跟家人提出转系,我想学中文系,研究文学史。我家人觉得我疯了,周围的人也几乎没有人支持。有人说,喜欢就去做啊,家人朋友的意见又如何。也有人说,喜欢也不一定当职业,可以业余搞。但不管怎样,说出这个决定,我承受的压力大概好比男同出柜。在此之前,我走在一条顺行道上,我努力的方向就是我家人和社会希望我做的。从此之后,我们的理想就分叉了。
我也曾想过是否可以业余,觉得还是不行。首先我比较认真,比较爱钻。为了钻一个事必然要花掉整块的时间。那种企业家宣称的“百战归来再看书”,后来证明都是扯淡。没有专业训练和一定的项目制压力,根本无法思考和工作。再就是社会也不允许了。科举时代读书是一个在城乡能否获得普遍尊重的生活,也是足以维生的手段。现在职场里读竖版书,人皆侧目。体制外的生存需要极大的毅力。当时肯定没有这么清晰,可还是决定转系。

转系考试在大一的下学期。那是2003年,正赶上非典。我周末回家就没能再回学校。等我再去参加补考的场次,那场只有我一个人。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天下午,响晴白日,我被安排在静园五院一间会议室里,题目是一张小纸条,两问:1.你为什么要转入中文系;2.翻译一段古文,是《孟子见梁惠王》。教务是个老太太,姓任,我进去之前跟我絮絮叨叨说了转系之后排课怎么麻烦,要从大一重新开始什么的。我坐在那里,这些事务性的问题就一直在我脑子转,最终心烦意乱,交了白卷。我一个人回了家,瘫软在家里的皮沙发上,哭,骂,骂别人,骂自己,直到日头西沉。
从此之后,我断了念想,但也和我家人谈好,只要拿到本科学位,考研由我决定。也就在那之后,我开始逃课,整学期地逃。我经常一个人跑到北海旁边的国图老馆,那时还不是古籍部,有一般阅览室。随便地读,中午在阳台上看北海的白塔。白天是爽了,晚上回到家里,翻江倒海的悔恨和自责。
大二、大三两年的暗无天日,远远的却有一颗明亮的星,那就是杨老师。从大一上开始,我选了哲学系杨立华老师的“中国古代思想世界”,第一次课讲的是一首北岛的诗,看不懂,老师讲了懂一半。往下讲先秦那些子,也不懂,但很独特。中学时代,我喜欢读文言文,可那只是个知识上的优势,比别人答题分高,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用,更没有觉得古代的东西“可以给现实的生活一个支点”(这是杨老师的原话)。大一下,我去旁听哲学系“中国哲学史”课程,那是通选课的专业版。正讲到魏晋玄学。杨老师写了一篇文章,题曰《在世的眩晕》,大概是用尼采哲学的一些概念重新诠释鲁迅提出的药及酒,一下把我讲懂了!!我从那里读到竹内好的《鲁迅》(那时的版本不是孙歌翻译的,好像是戈宝权,是个小红本),读叶嘉莹《汉魏六朝诗论稿》,读阮籍的诗。我的网名也就是从鲁迅的文学史提纲里得到的。酒·药·女·佛,这是四种事相,它所环绕的精神,就是我学问的初心。我迷恋那种东西,觉得人生就该那么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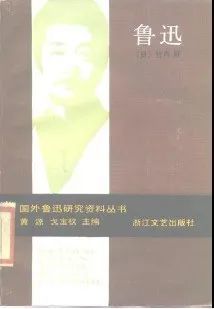
《鲁迅》【日】竹内好 / 李心峰 译/ 浙江文艺出版社 / 1986
大二以后,哲学系搞了本科生导师制,杨老师带几位学生读《传习录》,也叫了我。我记得当时,杨老师是所有北大老师里唯一一位能叫出我名字的人。从高三到大一一整年,我都只是一个学号,很难形容被老师叫名字时候的亲切和感动。
尽管杨老师和许多儒家一样,都对宋明儒者推崇备至。但我总之不好王阳明和宋明理学那一套。日后与杨老师的很多想法不一样,甚至有比较激烈的反应,但是心里一直觉得那是我在北大的启蒙老师,也是我做一个文科生的启蒙老师。
因为杨老师本科是浙大热力系的,我从老师的奋斗轨迹获取力量。最近在喜马拉雅上听他的《四书精读》,可能是有娃了,老了,格外喜欢回忆过去,以前对我们很少讲。我才知道杨老师跟我不一样,他是个强者,喜欢智力游戏,我是真怂,逃课了成绩一路往下。

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
我还庆幸有个有趣的室友,家里是音乐世家。外公是刘天华的弟子,父亲是二胡演奏家。但他父母早年离异,自己一个人在国内生活。他是北大民乐团的,我们都叫他团长。非典隔离期间,他家住在团结湖东方歌舞团的宿舍,离我家很近。他经常叫我去听琴。不只是二胡和笛箫,还有小提琴和钢琴。其实他更喜欢西乐。
后来我们就成了难友,到期末互相交流哪里可以借到笔记,哪门课比较容易挂人。也一起听课,比如杨老师的课。有一次他请我去听琴,晚上关了灯,点上一支小蜡烛。演奏完哭了,泣不成声。我说其实我们都有好学生基因,想做的事没有身份,不想做的事又不安于混,这太拧巴了。他表示同意。
在我决定考研之前,他有一个星期没有来学校。之后给我发了一条短信,说找到女朋友了。等来了我们问怎么回事,说是偶然梦见高中的一个同学,联系了一下就成了。女友当时考托福,他也跟着考。最终拿到了匹茨堡大学的off er,专业是ethnomusicology。临走前他挺自豪地跟我说,他是以史上最低成绩拿到奖学金的。因为他点儿背,本科挂了两门,最冤的是军事理论,五百人的大课挂两个,就有他。如此奇缘,只能说天降大任,天命难违吧。
二
我又怎么决定考英语系了呢?这事得从学法语说起。我和团长会互相推荐一些课,他也上杨老师的哲学史,我跟着他上了一门西方古典音乐。那绝对是北大消逝的美好事物之一。德语系一位退休的老先生,严宝瑜教授,当时八十多岁了,每周三晚上骑一辆小自行车,带着自己收藏的碟片到图书馆南配殿给学生边放边讲。

严宝瑜(1923年9月15日-2020年7月1日)
严老师跟我们说,年轻人要学好外语,最好多学几门外语。期末考试的内容是要听辨,用英文写出曲名和作者,还要考名词解释,其中比如idée fixe是法文,还有渐强、渐弱那一堆是意大利文,都要记住。因此我们几个上课的同学商量,要不辅修门二外吧。结果林云和戴翰程选了德语,我和杰阳、杨涛选了法语。
学外语我肯定算是笨的,尤其听说。但我特别享受这个过程,单纯学习的过程。就是前头说的,那种不分岔,只管向前的奋发。我们每天早晨到北阁北边那个小山坡念单词,坡这边是法语,坡那边是德语。然后一起吃早饭。辅修课程每周六课时,比专业都重,基本撑起了在校生活的节奏。我又重新做回好学生了。
特别感恩的是辅修还有外教,我们的第一个外教是巴黎高师的博士,Emilie,研究政治哲学和英语语言学,那真是班里男生女生的女神。按说第一学期学生的程度极低,可是每次课结尾,老师都会给我们听一首法文歌曲,发给我们歌词。有一次的歌词是魏尔伦的诗。这是我后来比如学日语从来没有过的愉悦,大家都喜欢学,喜欢那个文化,不是为了读文献,考TEF。
在考研的专业上我犹豫了很久。知道肯定不会留环院,但去哪里呢。杨老师劝我学哲学,可我不太亲近理学;也想考古代文学,杨老师说不如学现代,比古代易于借鉴思想资源。这是对的,所以也读鲁迅的研究,读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。可学了法语以后,人终于在一条现成的轨上。于是就想能不能再跑快点,直接报法语系呢?
当时班上有位助教何丹老师,我很喜欢她的风度。个子不高,也笑,但自有一种威严。班上有几个调皮捣蛋的,不敢冒犯她。她跟我说为我考虑,英语系更好,毕竟学习多年,而且辅修法语作为二外,成绩比英语系本系的有优势。事情就这么决定了。为这个决定,我也几夜睡不着,最终感冒一场,几无生趣。
这里边还有一个我最歉疚的事,便是辜负了韩老师。我们专业和地理系同属环境学院,地理系下设历史地理。我们都听说历史地理课老师讲课有意思,而且成绩不担心,平均85以上。韩茂莉老师讲话慢条斯理的,一个频率,像念稿子一样精炼,但其实没有稿子。上课倒也罢了,主要是韩老师对学生特别殷切。她有一些很固执的想法,比如本科最反映学生的智商,又比如理科生脑子比文科生清楚。智商高而脑子清楚,是做学问最重要的条件,什么基础知识都可以后来补上。历史地理在我们系是边缘,可按照韩老师这个标准,只要对历史地理表现出兴趣,韩老师都会像个宝一样地培养。

韩茂莉,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
原来韩老师家和我家在一个小区,我经常和韩师谈到比较晚,然后一起骑车回家。两年以前转中文系没成留下的种种困惑,学文科生计没着落,家里人不支持,做学术辛苦等等世俗的担心都说了。真像一个孩子和家里大人谈话。以前哪想过有个北大教授能听自己说这些破事啊!那个时候,我好像真把北大当家了。
后来等我报考了英语系,同学问我为什么没保送历史地理。我大概意思是说,仍然觉得历史地理的学科定位比较暧昧,和理科脱离得不干净,不是传统学问。我想做纯人文的学问,再不想和理科有半分瓜葛。话传到韩老师耳朵里,把我叫去痛斥了一顿。韩老师当时非常自信地说,中国传统学问如果有什么还对现代学术有价值,那就是历史学。你觉得历史地理是个舶来品,只能说读的太少,根本不会读书。古人的思想是在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,不是极有心的人根本发掘不出来。然后顺口给我举了四五个例子,从上古到近代,都是有关农业地理,种麦子之类的事。又说,英语系的人只掌握一门外语而无专长,你们现在条件这么好,自学也能办到,那样的话英语专业就不是专业,和文盲没有区别了。如果想做研究,没有一技之长,怎能自立?
我当时也很冲动,我说第一,不能因为中国乒乓球打得好田径不行,我们全部运动员都打国球,不练田径。喜欢的东西不计较成败。第二,英语系不是文盲,除了语言技能,语言配套着一种世界观,一种新的思维方式。最后韩老师也同意了我说的第二点。
这件事最令我汗颜的是,我考上英语系,又离开英语系回去做历史,回也没有回历史地理,还是坚持纯人文,两次都是韩师帮我写的推荐信,而且跟我说,你以后也要注意从地理的角度去看问题,毕竟在系里学过,都忘了也有基础。这种老师恐怕天下不易寻吧。再说句得罪人的话,恐怕只有北大才有。
三
决定做了,就要实施。北大外院有个特别的规定,本科生的课资源有限,严禁旁听。我和杰阳两人只能去大三、大四的专业课,有时也会赶人的。不赶人的只有Rendall老师的《神曲》课。阮爷爷一副圣诞老人的模样,很负责任。上课只能听懂10%,第一节课是介绍天主教的基本教义。老师布置说我们每次读两个canto,我不知道canto是什么意思,解释了半天才明白。
另外一门是丁宏为老师的英国文学史(下),从华兹华斯开始到20世纪,教材是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。丁老师的口语比较慢,但内容深邃。个别时候用中文表达。逐渐熟了我们就说了要考研的想法,看他作为系主任有什么建议。丁老师说,考研现在成了一种文化,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,我只建议你们,用心读专业的书,不要相信那些。语言能力和思考能力是分不开的,阅读细节是唯一的方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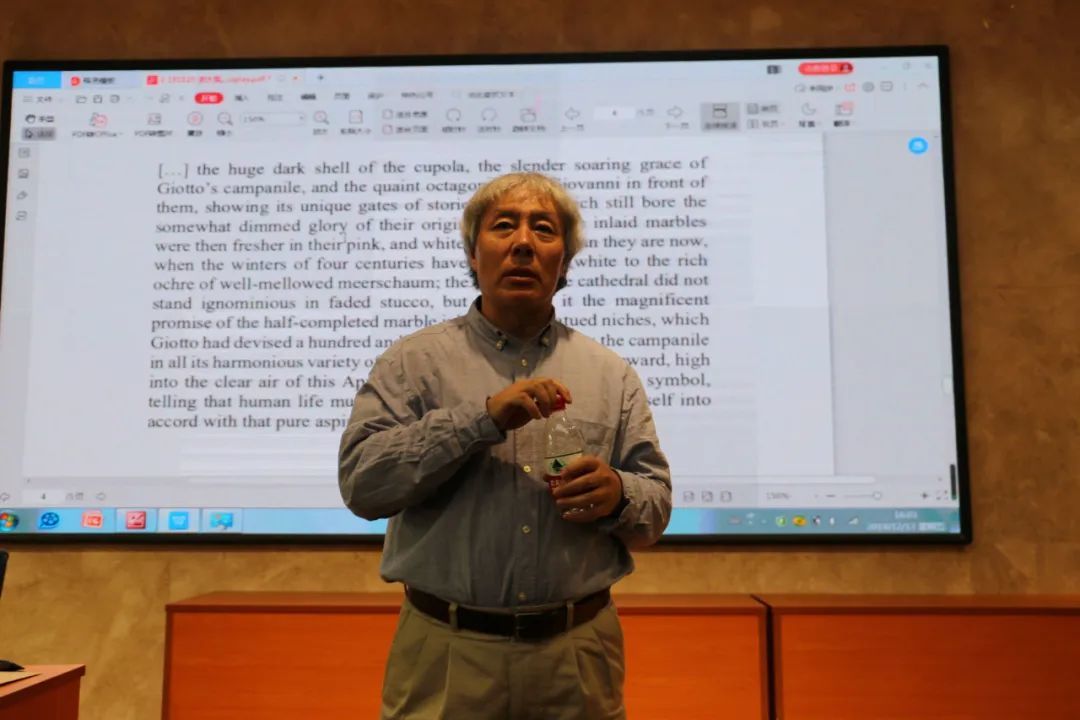
丁宏为,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
我们就去分头准备了。2005年暑假,我对照汉译本和Bantam系列的英译,把《神曲·地狱篇》反复过了四遍。注释也看。开始用韦氏词典,后来用金山词霸之类的软件,又回去用韦氏。然后是《诺顿文选》里的major authors,但没有中译就差很多。人不是机器,总有累的时候,那就看《余光中全集》,里边谈翻译的文字很有意思。其中提到董桥的《英华沉浮录》,意外地在书摊上买到一套。对中文和英文的特点若有所悟。
开学回来,才知道杰阳那边好像是把和合本圣经《旧约》读了,至少摩西五经都看了。我又开始读马修·阿诺德的《文化与无政府状态》,这次不特别需要对照了,但是韩敏中老师的译本太典雅了,爱不释手。考上以后有机会上过韩老师的课,很着迷那种上海式的叙述节奏,英文表达意犹未尽就换中文,中文不够又讲英文。我才明白,原来在文选里读的那些,也差不多是系里几位老师的理念,也部分影响了我。不仅仅是思想,还有文体的趣味和思考习惯。他们都反对才子气泛滥,韩老师说,The impressionistic criticism interprets nothing。从此,要有人觉得文学研究就逞才使气,就是凭感觉瞎说,我只能呵呵。
9月开始,去报了考研班。那体验真的挺辛酸的。上课地点在中央民大一个大礼堂里,约有一千人。厕所在门外,很小。中午听课的人出去吃泡面,和厕所的味道混在一起。讲课是人大的陈先奎,极其粗鄙,在台上说我年轻的时候最喜欢哲学,诗歌云云。也说不上厌恶,只觉很荒谬,哭笑不得。
整个培训也就十天左右。考上以后说起这段,丁教授表示很不屑。他考过两年,还要找住处,比我辛苦一万倍。不过重要的是,硕士英文,博士历史,由于地利之便分别参与过考研政治和英语的阅卷。细节就不讲了,怕惹事,我们的结论是,与其准备怎么答题,怎么写作文,不如买本庞中华书法字帖把卷子写得顺眼点儿……

四
考上可真是侥幸。我那年只有三道题,第一题是分析诗歌。作为考研生活的调剂,我上了陈怡怿老师的《圣经》和胡续冬的诗歌课。课上恰好讲过一首爱尔兰诗人Seamus Heaney的诗,就是我们的考题。诗里有些不认识的词,要是没讲过,分析起来会很麻烦。第二题是谈《圣经》对文学的影响,略具常识总有话说。第三题忘了。北外的卷子都是考基本功,一堆选择、完型,跟高考一样。我们之后北大英语系是七道题,还有美国文学和文论,不能选答。我是托了考题粗放的福混过去的。遗憾的是,和我一同考研的杰阳却没上,他水平比我高,对诗歌的感觉也比我好,也有热情。造化弄人。现在中大研究诗经、尚书之学,也算托身得所了。
英语系的考研率极低,从环境学院转来英语系,从理科生变成文科生,这是我人生最自豪的经历之一(另一次是去京都大学访学,以后有空再谈吧)。此前高考能上,因为学校是重点,北京分数又低;此后换到历史系,除了老师眷顾,只是日常积累而已。唯有这次是在全无外力的环境里独立支撑做到的。当时被问及考不上怎么办,每每引“明朝散发弄扁舟”之句搪塞,真要怎么弄,自己也没想法。
要描述我在英语系学到的东西是困难的,我本想继续写下去,但感觉有些气弱。我只能说,在那里形成了世界观。以我英语水平之差,在外人面前有点羞于谈起自己是英语系出身,可我内心又无比认同这个身份。我还想说,那段时光也是我最安适的读书时间,这与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关。对这个社会来说,本科的竞争力不够,博士又成了怪物,他们看着最顺眼的就是有点专业技能的硕士。我本科既然别扭,博士更是十恶不赦,硕士三年便成了与家庭、与社会关系最为缓和的时期。使我得以从容地读我的书,考虑我的未来。
人生七转八弯,好像长了反骨,在我自有内里的逻辑,这也难说。确对环境有各种埋怨,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,就是总比本科四年好!那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,孤独,荒谬,虚无,迷茫,为了克服那些,我结识不同个性的老师、学友,在家庭之外构筑自己的小世界。我要确保,当我一个人去答那张卷子的时候,我不会再因为软弱而放弃。
脱脱不花(陕西师范大学翁彪老师,是我的挚友,平时称呼其网名。)展示过《新华字典》的一個例句:“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;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;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: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。”(1998修订本,第673页)这也是我通过考研要实现的梦,在外人看来,这是个熊市,是人往低处走,是从朝阳走向夕阳,可在我看来,众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。随着学术兴趣的转移,我从英语转历史,做佛教接触哲学、艺术,未来也会重拾六朝文学的研究,但那是丸之走盘,我再也不是理科生了,我再不用坐实验室了!志愿是我填的,但我赎身了。我要去争自己的光明了。
只要人生不是数字的比较,不就都有奔头的么?

本文节选自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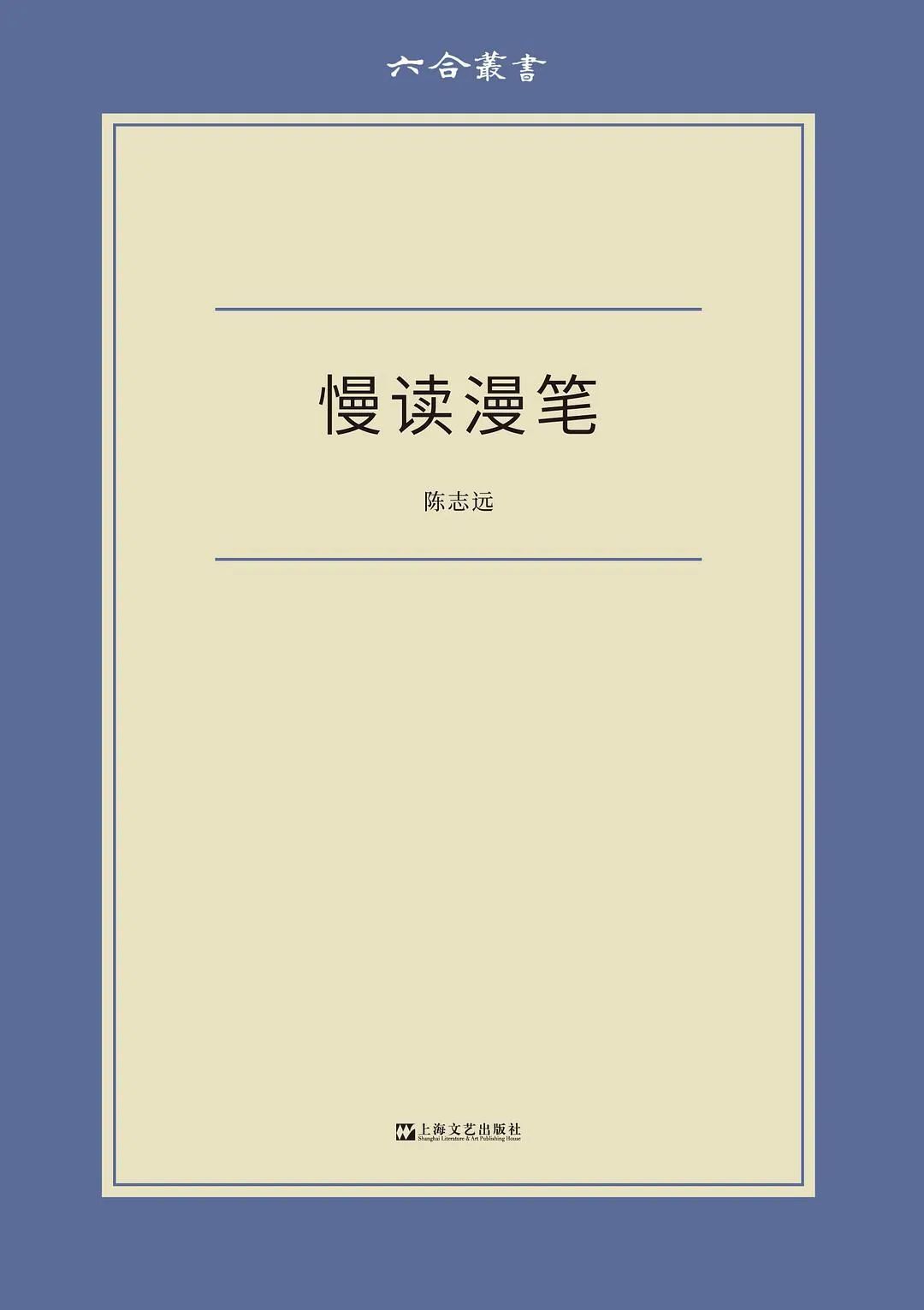
《慢读漫笔》
作者: 陈志远
出版社: 上海文艺出版社
出品方: 艺文志eons
出版年: 2020-4
来源:凤凰网